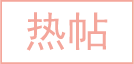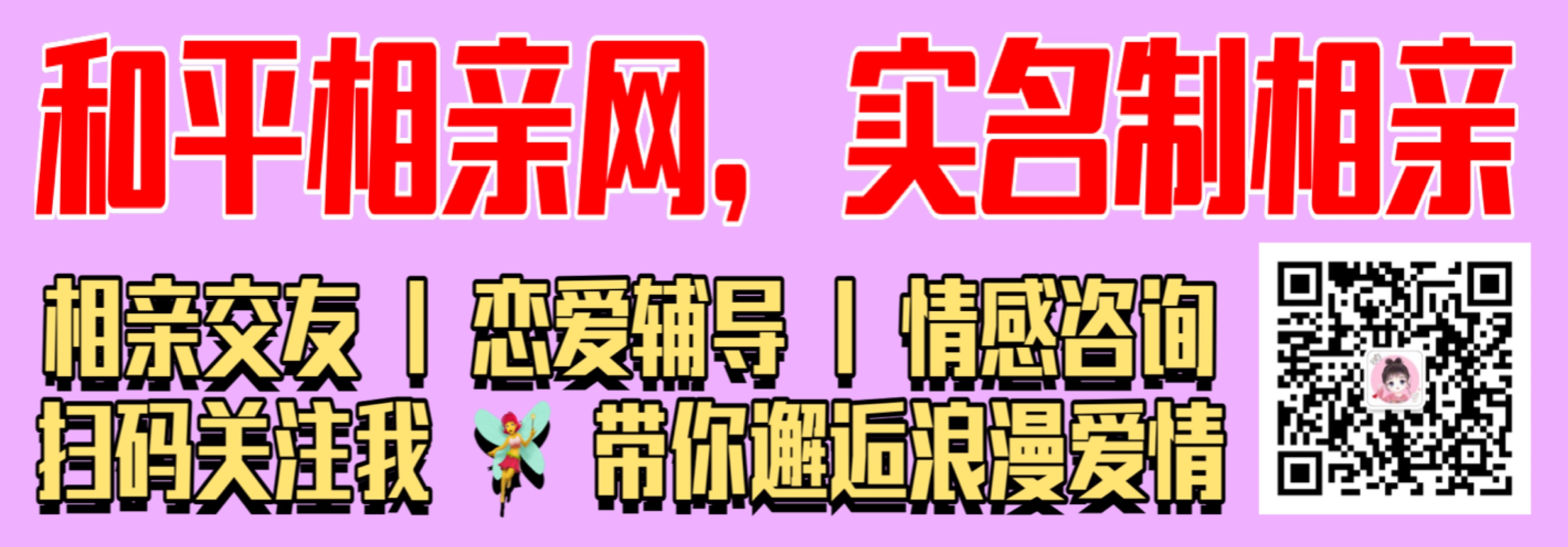每织出一段布后,年轻女子总要认真检查每一根经线。女子说如果经线断了,就算能接上,织出来的布也会有痕迹。肖斌 摄
关于“墩头蓝”在明、清朝至新民主革命时期和解放后以前一段时期,墩头村利用本地的天然植物大青叶,应用独特工序制作、染料,运用先进的织布技术和耕织、纺织技艺,制作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纯天蓝色的家机布料。“墩头蓝”因出产地名为“墩头村”,故民众尊称为“墩头蓝”。

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织布机上熟练操作抛接布梭。肖斌 摄
正在申报省非遗项目“嫁郎爱嫁墩头郎,又会织布开染房......”世代传唱的客家山歌民谣
从和平县彭寨镇墩头村的一座古厝传来,在古厝外的屋檐下,11位墩头老媳妇正在晾晒打好的纱筒和唱客家山歌。
走进这座古朴的农家小院,两位老人正在院落里用两手打纱筒。在厢房内古旧的织布机前,“墩头蓝”布艺制成的帽子、衣服、头巾、面纱等日常生活用品独具特色,它们见证着墩头村织布业曾经的辉煌。织布的老人抬头问明来意后,便讲起了他们与“墩头蓝”的故事。
据了解,71岁的老人叫曾凡度,从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织土布技艺,如今已经坚持了50多年,从未中断。另一位老人叫曾凡希,今年72岁,16岁开始随家人织布至今55年。“在清朝乾隆35年,织布染坊的前身是东江第一儒林·梅园书屋”。曾凡度说,在嘉庆10年,本地曾姓后人在凑钱出资修缮梅园书屋后,集中传授织染技术,将以“墩头蓝”为特色的墩头村明清传统布艺,推向荣耀的顶峰。

墩头村的老媳妇熟练地使用着纺车,棉花条在嗡嗡作响中变作纤细的棉线。肖斌 摄

棉花纺成棉线后需要按顺序排列整齐备用,这就是挂在织布机上的经线。肖斌 摄
至今,从事明、清传统布艺“墩头蓝”人事、物件仍在,是传统的魅力,让人追溯。歌曰:“嫁郎爱嫁墩头郎,又会织布开染房......”世代传唱的客家山歌民谣,折射出当年墩头村等周边村落民众耕织持家、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墩头蓝’棉纺印染布料以整洁柔软、厚密有度、耐磨等特点。”曾凡希说,“墩头蓝”布料、布艺成品也因此行销东江流域和邑及邻县各墟镇。
在老房子的大厅内,有几位老妇人在熟练地使用纺车,棉花条在嗡嗡作响中变作纤细的棉线。走进另一间厢房,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织布机上熟练操作抛接布梭。“在封建王朝时期,手艺活是一家人的饭碗,都传男不传女。”曾凡希介绍说,现在是新时代,打破了封建观念,不少年轻人和女子都加入到织布技艺中来。
据资料显示,“墩头蓝”织布技艺在当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至今仍有“墩头蓝”织布出售。和平县文化部门计划今年内将该织布技艺申报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来源 | 河源日报
作者 | 肖斌
自助阅读和平“墩头蓝”去哪儿了?
乾隆喜爱的工艺
织布机还在,织布工匠早已作古。和平县彭寨镇墩头村的曾姓后人们,不敢让这项传家手艺消失,他们的祖先可能正是织布好手,也曾亲身参与数百年前的未有之变局,就像他们面对如今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和平县文联资料记载,曾氏祖先曾官大做过江南通判一职,那里的织染品深受清代乾隆皇帝喜爱,更为曹雪芹文学创作提供了繁华背景。
曾官大带着江浙织染技术告老归乡,为家乡织染业带来了一次技术革命。
如果有人带着摄像机采访过曾官大,记录当时的生产、染布和买卖就好了。事实是没有。墩头人不喜欢虚妄崇拜,他们将留下一座梅园书屋的曾克常视为祖先,他们称自己是梅园公的后代。尽管克常先生只是个教书匠,也没有资料能证明他与织染布的联系。

曾凡度和曾凡希两位老人正在院落里用两手打纱筒。肖斌 摄
“嘀嗒”陪伴一生
71岁的曾凡洛先生给出了他的判断,织染布也好,读书科考也好,祖先并不看重后人做什么,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曾凡洛是个织布好手,手艺是父亲手把手教会的,面容清瘦,会刨光饭碗的每一粒米,听人说话极富耐心。相比父亲的执着,改革开放初期,曾凡洛的双手告别棉纱转而操上了剃头刀。
曾凡洛记不清父亲曾庆焕去世的具体时间了,一片嘈杂声中,老人的死亡年限被多数人认定为2011年,曾凡洛有些疑惑地补充到,“父亲去世时已经92岁了。”
尽管儿子改行,老人的时光仍耗在织布机上,他每天仍与“滴嗒声”为伴,窗内只剩白织灯映照下的宁静,工业纺织品早已完成对市场的占领,消费者热衷满目琳琅的选择,他们轻松忘掉了曾经“地下交易”的紧张。

墩头老媳妇正在晾晒打好的纱筒和唱客家山歌。肖斌 摄
计划经济下的交换
在本该属于曾庆焕的年代,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计划经济通过指令而非市场需求指挥织布机的转速,国家印发的“粮票”、“布票”、“理发票”……替民众决定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像一张能买通一切的通行证。
曾凡洛私下卖过布,他游走在计划经济以外,卖价比布票的定额便宜20%。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是“投机倒把”。幸运的是,在这个受近代商业文明浸润的远离政治中心的村庄,即便被抓了现行,也没有多少政治负担。60出头的曾金练是个熟络的包工头,他也帮父亲卖过不少布。那时他挑着箩筐,靠编织袋打掩护,“商品”躲在下面,走到哪就卖到哪。
事实上,躲的又岂只是布,曾凡洛、曾金练及更多未署名的村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父辈劳动的价值。

一根棉线断了,老人灵巧地接上。肖斌 摄
父亲唯一的遗产
上世纪80年代,曾庆焕以象征性价格从政府手中买回织布机,这个熟络的工匠以每天制造8万次“滴嗒声”节奏来安排生活,直到三年前去世,织布机从此永远安静下来了。
在工业品来袭、传统手工业江河日下的90年代,曾庆焕一直将棉纱线捏得很紧。在这里,他担当过一家之主的角色,他的喜怒哀乐都留在织布机上。
这架连续服役100多年的老家伙,去年底搬到了墩厚围。曾凡洛试图给记者演示织布的场景,只见他换了两根竹条,拧了拧一些阀门,仍未成功。
织布机还留有父亲生命的遗作,那是一段长约1米的成品布,另一端的25米棉线未及成形,主人便匆匆离世。曾庆焕没给后人留多少遗产,一台织布机,一匹20多米的成品白布,也有做人的道理。“这是父亲唯一的遗产,我要传下去。”这个古稀老人认真地说。

在每一卷经线被放上织布机前,老人们总要反复检查,细致入微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肖斌 摄
“墩头蓝”大染缸
事实上,棉纱线纵横编织而成的白布,遇上蓝树果子流出的蓝色汁水,墩头曾氏的织染布工艺才称得上完整。如今距离最后一批白布与蓝色融合,已经过去好几十年。谁也说不清树种在当地消失的原因,除了墩厚围门前躺着的用来使布料颜色均匀的三块“元宝石”,染布工艺流程恐难再现。
曾姓村民为祖传工艺取了个典雅的名字:墩头蓝。就像山歌唱的:嫁郎爱嫁墩头郎,又会织布开染房……事实是墩头郎开染房,买卖赚钱是首要目的。

在古厝外的屋檐下,11位墩头老媳妇正在晾晒打好的纱筒和唱客家山歌。肖斌 摄
从四到六,跨越断层
曾庆焕去世后,“墩头蓝”第三代传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据说村里还有一位老工匠,但也很久没摸过机器了。曾凡洛等10多个村民帮衬过父辈织布,如果严格按“耕布—梳布—织布—染布”标准,真正的传人屈指可数。
曾凡洛归属于“第四代传人”,是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另一方面,六十岁以下的人,也就是本应该被称为“第五代传人”的人们,但都对织布机感到陌生。
“墩头蓝”传到第五代断层了吗?村民们并不否认。墩头村去年10月决定采取传统工艺抢救行动,从村里挑选16至20岁的曾姓后人学习织布,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成为跨越断了层的第五代的“第六代传人”。“已经有20多人愿意学习,我也是老师。”还没等说完,曾凡洛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试想一个泥腿子走上讲台的感受吧,他果然是梅园公的后人。
来源 | 河源乡情报
作者 | 周秦